競業協議,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詞,在互聯網急速發展的那幾年,競業協議成為企業保護自己商業機密的“標配”。而如今,互聯網行業逐漸趨於平穩,但競業協議卻在被擴大化和濫用,勞動者們被“層層設局”,卻無法掙脫。

有人在跟蹤。
劉欣突然心跳加速,她知道大概率是幻覺,但是忍不住時不時回頭看看。這樣的事情曾經發生,2023 年,前東傢派人連續一周拍攝她從傢到新公司的視頻,作為她跳槽到競對公司的證據之一。
那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和他手裡的攝像頭,具象成仲裁判決書裡 2500 元的調查取證和公證費,但在共計高達 28 萬元的賠償金裡,顯得並不那麼重要。
即使換城市,換住址,“ 從我離職的那刻起,他們就沒想放過我。”
2022 年 6 月畢業的劉欣,進入這傢增長迅速,驟然升格為 “ 大廠 ” 的公司。HR 以校招 HC 有限為由,以社招方式向劉欣遞出橄欖枝,劉欣同意,入職公司廝殺正酣的團購業務,工作地點在廣西南寧。
實際上,劉欣對這傢公司高強度的工作也有耳聞,明確的知道這裡實行 11-11-6 的工作時間,但她覺得剛畢業,可以鍛煉一下,苦還是要吃的,至少幹個一兩年。
采銷專員的月薪一萬零八百,到手 9000 多塊,每天上午十一點從比價開始,調價、對接上百個商傢,聯系商傢備貨,催促入庫。一般最後一批貨品入庫是在凌晨 12 點,但大部分情況不會這麼順利。
同時,公司新人也有一天工作結束後寫日報的習慣,要求事無巨細,需要分析自己類目的每一種貨品當日的銷量情況、原因、改進,對比隔壁區域同款產品銷量情況、原因、改進,劉欣寫 5 個月。有一段時間,完成所有工作後,劉欣都是哭著下班離開倉庫 —— 為方便辦公,公司的工位就在倉庫裡。
劉欣想起當時企業微信的推送,會顯示每天多晚還在處理信息,她隨便翻看一下,時間都在凌晨 12 點到 3 點左右。超負荷工作唯一的好處是每天睡得很死,沒什麼時間想別的。
她還是沒有堅持到一年。 8 個月後,2023 年 2 月,在體檢指標 43 項飄紅後,劉欣提出離職,時至今日有項病癥她依舊需要每日服藥、按月復查。
離職前,她提到 HR 要求她簽署一份競業協議,啟動後競業補償金按在職月基礎工資( 8100 元)的 30% 發放,也就是每月 2430 元。如果違反協議,則要賠償公司 24 個月的月工資並返還已發放的競業限制補償金,共計約 28 萬元。
初入社會的她並沒有過多猶豫就簽,因為 “ 否則無法拿到離職證明。”
這看起來很合理,公司向離職員工發放補償來保護自己的商業機密,員工領錢就要承擔起相關的責任。
但,在實務之中,大廠們競業協議的范圍在不斷迭代。2020 年左右,合同中基本上為有限列舉的公司,之後就開始不斷擴大:持股公司、上下遊公司都被囊括其中,甚至進展到粗暴的用營業執照的字面經營業務重疊來定義是否違反競業協議。
劉欣的公司的競業限制期為 9 個月,這份協議裡幾乎囊括大部分互聯網公司和電商平臺,及其關聯公司、為上述公司直接或間接提供服務的企業以及投資上述公司( 或被上述公司投資 )的企業或經濟實體。
舉個例子,劉欣雖然是買菜事業的采銷專員,但如果她離職去《 王者榮耀 》所在的天美工作室做一名後勤人員,理論上也是能命中競業協議的,因為天美工作室是被騰訊所註資的。
簡而言之,招聘軟件上隨便刷到的公司都有可能是競業雷區。
也就是說,這份看似合理保護企業自身的協議,以合法的手段,在用每月 2430 元的競業補償,鎖定一名畢業不到一年的大學生生命之中最重要年華的 9 個月。在快速迭代發展的互聯網行業,如果十分嚴格的遵守,她會與整個互聯網行業無緣。
劉欣要麼拿著每月不到 2500 元的補償金在省會城市 “ Gap year ”,要麼冒著被巨額索賠的風險繼續找工作,作為一個從不知名小山村走出來的大學生,背負著全傢人希望的她,看似有選擇,但隻能選擇後者。
2022 年應屆畢業生柯林工作一年零三個月後面臨著同樣的抉擇,從事運營工作的他離職後因為入職競對公司被索賠 44 萬元。
最讓人超出認知的案例是楊越。他同樣在該公司擔任運營,在 2023 年 6 月從公司離職,他的基本工資為 5900 元,在離職前公司 HR 要求簽訂的競業協議裡,9 個月競業期,競業補償金按照基本工資的 30% 計算,每月隻能拿到 1770 元,甚至沒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
在發三個月的補償金後,楊越發現自己被公司申請勞動仲裁,原因是自己未履行競業限制義務,需要支付高達 27.6 萬元的違約金。
知危編輯部對此產生超出樸素認知的疑惑:
月薪 5900 元的最基層員工,真的會知曉什麼公司機密、並在出去重新找工作時對公司產生重大傷害嗎?

在 2023 年 10 月被公司索賠 28 萬之後,剛離開象牙塔的劉欣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作為勞動者的身份,以期更理解自己的處境,她的疑問層層展開,又隨著事件的進展一步步陷入絕望。
自始至終,劉欣都不認為自己該被競業。 她詳細地解釋自己的工作內容,覺得自己作為應屆生進入公司,在職級上也屬於基層員工,不屬於競業限制的范圍。《 勞動合同法 》第 24 條規定,競業限制主體限於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業務的人員,且競業限制期限不得超過兩年。
但是該公司認為劉欣掌握公司的商傢信息、招商方案、市場數據等機密數據,所以屬於 “ 其他負有保密業務的人員 ”,仲裁委員會支持這樣的說法。
其次,在仲裁中,劉欣們都提到協議的簽訂 “ 非真實意思表示 ”。實際上,在勞動者與企業權力和能力儲備不對等的情況下,劉欣突然被叫到封閉空間內簽署協議,有某種 “ 迫不得已 ” 的意味。
但以 “ 脅迫 ” 為由撤銷合同,本身舉證難度和證明責任極高,得到司法認定很難,不要說是她這樣涉世未深的應屆生,即使是工作多年的員工,也無法做到。
上海眾華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胡曉光律師向知危編輯部分析取證的難度:“ 首先勞動者無法提前預警,做到隨時錄音,其次即使錄音,記錄下存在脅迫的語言內容,公司從應訴技術的角度也可以完全否認說話內容的真實性,最後公司完全可以說協商隻是過程性溝通,但員工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還是簽署書面協議,應當以書面約定為準。”
但同時,協議也並非完全不對等,約定的企業每月固定發放的競業補償金體現公平原則和對勞動者的保護,即使 30% 的月工資看起來金額並不高,但合乎法律。
另外,還有一個爭議點。劉欣覺得自己雖然入職競對公司,但工作內容已經從買菜業務轉移到海外業務,並且品類與針對人群皆不相同,所以並未違反競業限制約定。
而這一點,其實更難自證。
“ 法官的裁判邏輯認為,人的技能和思想是潛移默化的,如果進入新公司,完全從事與過去知識儲備與技能不相關的工作,根據人的社會性和積累知識角度來說,進行完全的知識技能切割往往違背常理,所以法院一般不會支持這點。” 胡曉光律師如此解釋。
這些其實是大部分有類似經歷的勞動者在面對仲裁或訴訟時,都會提出的異議,但是獲得法院支持的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關於劉欣們簽訂的協議,大多數司法實踐依然以形式上的合同約定優先。以競業限制的人員范圍為例,當法律對第三類 “ 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 ” 沒有明確概念時,用人單位的格式條款就成為優先采納的依據,這個模糊化的地帶被公司方 “ 占領 ” 。
作為一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一旦你簽下這份競業合同,日後出現糾紛,在競業限制協議事實清楚的情況下,勞動者敗訴的結局幾乎是註定的。
其實,在法學界,已經有學者意識到我國裁判事件中僅關註競業限制義務是是否履行的事實,而模糊對協議效力的審查。也就是說,現行協議效力審查規則不涉及對協議內容合理性的實質審查,這就導致很多合同內容和競業范圍在明知不合理,但依舊被法院認可的情況。
武漢大學法學院喻術紅教授曾整理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5 月的 454 份與 “ 競業限制 ” 有關的民事判決書,其中 87% 的裁判確認或默認競業限制協議有效。她認為,實際上,這些協議雖然形式上合法有效,但實質上存在主體泛化、限制范圍不合理、權責不對等等問題,可履行性存在爭議。
並且,在競業限制義務主體中,79% 為 “ 負有保密義務的其他人員 ”,裁判實踐中該類主體的認定頗為寬泛,法官也鮮有涉及這類主體的抽象概括與特征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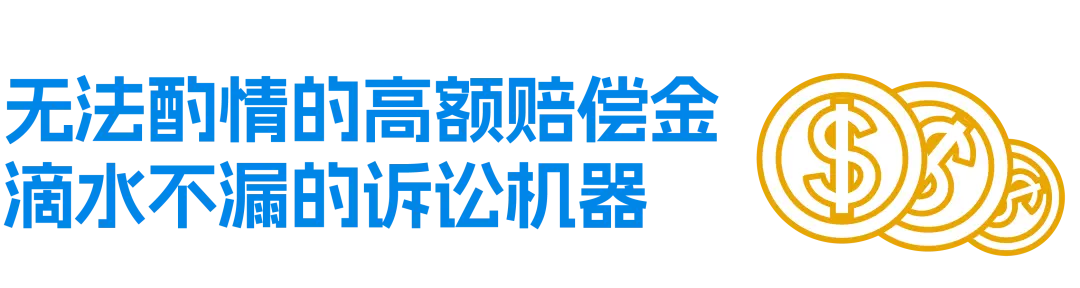
那麼,在敗訴註定的情況下,劉欣要爭取的是什麼?
答案是違約金金額。
從個案審判實踐來看,有學者對 2018 年到 2020 年上半年 102 起代表性離職競業違約金糾紛判決書進行統計,發現法院未支持酌減的 18 件,支持酌減的 84 件,體現出高違約金的普遍現象和法官支持酌減的普遍傾向。
姚明斌的《 違約金的雙重功能論 》裡提到,用人單位普遍有意約定明顯過高的違約金,甚至在明知超出一般勞動者承受能力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如此,體現出其更加重視違約金的懲罰屬性,以及試圖借此震懾勞動者嚴格履行競業限制義務。
胡曉光律師認為,法官支持酌減的考量因素主要是勞動者新舊工作的內容和性質、在公司期間的經濟收入與競業限制協議約定的經濟補償金數額,以及給公司造成實際損失及大小情況。往往在用人單位無法證明損失的情況下,酌情減少,一般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范圍。
但,詭異的是,知危已獲得的包括劉欣在內的多位涉及該公司的基層員工仲裁判決書均顯示 “ 頂格處理 ” ,也就是在確定勞動者存在違反競業限制的行為後,完全支持用人單位的高額違約金訴求。
知危查閱資料時也發現一個可以對照的案例。來自蘇州法院最近公佈的 2018~2023 年競業糾紛案件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中的一起,離職前十二個月平均收入約 6000 元的單某,與某高分子材料公司簽訂競業限制協議,約定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違約金為 100 萬元,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為 1220 元/月。
其離職後入職同業競爭公司,後公司經仲裁前置後起訴至昆山市人民法院,主張單某支付競業限制違約金100 萬元。
昆山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公司未舉證其損失數額,雙方簽訂的協議約定的權利義務明顯不對等,違約金明顯過高,應當依法予以調整。綜合考慮單某的職務、違約情節、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額等因素,並適度體現對勞動者違約行為的懲罰性,昆山市人民法院判決單某支付競業違約金4 萬元。
這也正是令劉欣崩潰的地方。 多地案例和過往經驗,讓其代理律師曾判斷為賠償金額不會如此之高,並傾向於會通過仲裁庭調解完成,沒想到用人單位金額要求過高,調解未果。
一位上海的律師向知危坦言,法官或仲裁員判案的底層邏輯來自於 “ 不錯判 ”,畢竟書面協議在先,從裁判正確的風險度考量,按照合同金額裁判,保證案例的底線,但是法官如何使用自由裁量權進行酌減,確實不同地區、不同法官會有不同判罰。
也正基於此,劉欣和律師決定繞過勞動仲裁所在地上海市長寧區,通過向社保繳納及實際工作所在地廣西南寧提起訴訟的方式,以求得更公正的裁決。
此時,讓人絕望的事情出現。
2023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2 點左右,劉欣和律師收到頂格賠償的仲裁判決書,當天下午四點鐘向南寧市某區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請,並在 12 月 25 日立案成功。但是在 2024 年 1 月 5 日獲知案子又被移交回上海市長寧區法院。
劉欣這才發現,12 月 1 日上午,該公司不服仲裁裁決書,向長寧區法院提起訴訟,她在當天上午 10 點鐘左右收到長寧區法院的短信。
這裡需要科普一個規則,有時一些案件出現糾紛合理爭取屬地管轄權十分重要,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 “ ……雙方當事人就同一仲裁裁決分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的,後受理的人民法院應當將案件移送給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 的規定。
也就是說,從時間上看,劉欣不僅在得知仲裁結果上比公司要晚,遵循哪裡先立案哪裡先受理的原則,劉欣申請立案時間也要晚於對方。
“ 12 點才知道仲裁結果,如何提前就能申請立案?這對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值得一提的是,仲裁判決已經基本支持用人單位的大部分訴求,劉欣的辯護律師認為,此次起訴,完全是為搶奪屬地管轄權。
知危在梳理案例的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這傢公司在對待離職員工,打競業官司上,具有高度流程化和不斷迭代的特點。
在裁判文書網上,2023 年 4 月一起該公司的競業限制糾紛中,勞動者成功提出管轄權異議並從上海市長寧區法院移送至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處理。而至少在半年後劉欣的案例裡,這樣的操作已經不可能,2024 年 1 月 29 日,柯林的裁決書出結果後,也出現同樣的情況。
在其他大廠的勞動合同糾紛中,面臨競業補償金沒有回旋餘地的境地,有些勞動者會通過訴訟索要在職期間的加班費挽回損失的案例。
但,在劉欣所在公司的勞動合同裡,明確寫明 “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資,已經包含有關法律規定及有關政府部門規定的各類補貼、津貼在內。” “ 如乙方對當期工資有異議的,應在收到工資後 3 日內向甲方書面提出,乙方在上述期限內未對當期工資提出異議的,視為當期發放工資準確無誤。” 這兩條款直接扼殺該企業勞動者索要加班費的可能。
劉欣徹底絕望,加班的日夜時間像個笑話。
值得一提的是,外人無法知曉到底有多少基層員工被該公司啟動競業協議,胡曉光律師提到,競業合同糾紛有相當一部分都以調解或私下和解撤訴的方式結束,案例無法呈現在公開平臺。那些稍有傢境的勞動者很有可能吞下這個苦果,最終展現出來的,隻有劉欣這樣的 “ 苦命人 ”。
劉欣覺得她似乎一直在一張密不透風且光滑無比的墻面前打轉,“ 明明不合理,但沒辦法訴說。” 到目前為止,這場博弈隨著常識的不斷被打破,似乎註定結果。劉欣、柯林、楊越均處於不服勞動仲裁結果的一審階段,有相似經歷的他們成立 “ 打工者聯盟 ”。
在這裡,他們發現,就算是經驗豐富的職場人,也會被超出認知的競業協議限制所困擾。

於楓是一名互聯網老兵。他怎麼也沒想到,在 2 年競業期即將到期的最後幾天,自己被公司起訴違反競業限制協議,被要求賠償的違約金非常巨大,對很多普通人來講是一個天文數字。
2018 年於楓入職公司,offer 明確規定年薪中 50% 為股票期權。入職半年後,於楓被要求簽訂一份補充的競業協議,他發現協議將原來工資中的股票收入定義為 “ 競業限制的對價 ”,離職後若其違約,公司將有權收回尚未出售的股權激勵,追索所有出售股權激勵所生之收益,無論該股權激勵已出售多少年,且員工不得要求返還已繳納的稅款及已支付的行權款。
於楓感到這明顯是不合理的條款,但又別無他法,“ 當時我已經入職半年多,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團隊,我無法做出拒絕簽訂離職的決定,那時的沉沒成本太高。”
文件篇幅很長,於楓無法完全閱讀,也被告知不許拍照,“隨大流吧” 經過考慮,他選擇簽下自己的名字,也為之後的事件埋下伏筆。
2021 年初,於楓從公司離職,由於股票分批解禁,離職時於楓拿到 50% 的股票。
離職的時候非常順利,並沒有像其他案例一樣被要求簽署新的競業限制協議,於楓表示公司也並未告知自己是否啟動競業,他甚至還記得最後一天的時候,HR 和他分別時還說句 “ 祝你工作一切順利。” 之後他嚴格按照對方口頭提出的要求執行:不發朋友圈,不請客吃飯,不與在職同事聯系溝通。他靜默。
離職後的日子於楓一方面開始創業,經營狀況並不好,前期幾乎沒有流水,之後月流水也剛破萬。另一方面他決定用積蓄在上海買房。
不過,由於社保積分較低,於楓連搖幾次都無法入圍,為提高中簽率,他在朋友的一傢公司代繳社保。三個月後,房子搖到,於楓停止社保繳納。 之後他一邊經營著自己的公司,一邊在傢照顧孩子。直到 2023 年初,被前公司起訴,由於當初代繳社保的公司以及自己創業的公司在經營范圍中都與前司有重疊,公司據此要求追索出售股權的收益。
律師和於楓認為,粗暴的用營業執照的字面經營范圍重疊來定義是否違反競業協議,是有爭議的,況且作為小微企業,在經營體量上與該公司差別甚大。
實際上,在立法原意上,競業限制措施應當遵循最小限度原則,即競業限制的范圍、地域和時間不得超出保護商業秘密所必須的限度。以競業限制的范圍為例,最高人民法院在 190 號指導案例中指出,“ 競爭關系的審查,不應拘泥於營業執照登記的經營范圍 ”,而應進行 “ 審慎且實際性的審查判定 ”。
2023 年 11 月,於楓的律師收到長寧區法院的一審判決,判決書基本認定於楓違反競業限制協議事實成立,支持原告公司的天價索賠訴求。之後,公司申請財產保全,於楓用於按揭還款的銀行卡賬號被司法凍結。
實際上,這樣的操作方式並非個例。為公司工作 4 年多的林浩也有著相似的遭遇,離職後被訴違反競業限制協議,同樣是以股票作為競業限制的對價 。2024 年 1 月,林浩用於還房貸的銀行卡被凍結。2 月 19 日,該案被長寧區法院定為 “ 疑難復雜案件 ”,一審需要較長結果。
實際上,股權激勵能否作為競業限制補償金在法律及司法解釋上並未有明確規定,知危編輯部發現各地司法機關存在不同口徑的案例。
反對理由主要在於兩點。一,股權分紅收益與競業限制補償的性質不同。股權分紅收益需滿足一定的授予條件,是否能夠行使權利、獲得收益均要受到限制,具有不確定性;而競業限制補償金是對勞動者離職後在競業限制期內因擇業權利受限所造成的利益損失的補償,不屬於員工的工資或者其他福利,與員工在職期間有無違紀行為等無關,具有排他性,且該補償金應為確定數額。二,競業限制補償應當在員工離職之後支付,屬於強制性法律規定,在職期間支付不具有合法性。
支持理由在於,法律並未禁止用人單位可以以非現金方式給付勞動者競業限制補償金,也未禁止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在職期間提前支付競業限制補償,即如果雙方在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就股權激勵作為員工履行競業限制義務的對價達成約定,因該約定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
從司法裁判相關案例審查裁判認定來看,若股票期權被認定為獨立於正常工資報酬以外的額外福利待遇,那麼其被法院認定可作為競業限制義務對價即競業限制補償金的可能性較高。
剛剛過去的春節,於楓險些面臨無傢可歸的境地。“ 我隻有起訴等待二審的判決,不然的話我的房產可能進入司法拍賣的程序。”
於楓今年快 47 歲。屬於較早的一批滬漂小鎮做題傢,經歷改革開放的巨變,之後擁抱互聯網浪潮成為大廠一員,在 42 歲時還擁有極強的職場競爭力,他靠著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擁有屬於自己的傢,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
但,崩塌仿佛在超越常識的瞬間產生。
那是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後的一周,於楓突然發現自己的聽覺消失。“ 對面的人和我講話,我隻能看到他的嘴在動,我聽不見聲音,但是周圍路過的汽車聲,路邊的狗叫聲又卻能聽得到。”
“ 你坦誠回答我,如果按照法條解讀,民事訴訟案件中,如果被告突然離世,是不是訴訟審理的過程會終止?” 於楓問律師一個問題。
“ 就算被告突然死亡,遺產也會被追訴的。” 律師沉默良久,還是決定回答於楓。

這些困於競業協議的人們,一起建立起一個 “ 打工者聯盟 ”,知危編輯部發現這個聯盟時,第一個接觸的人是林浩。
相較於其他重點關註自己案件本身的人,林浩對整個 “ 聯盟 ” 有一個更群像化的觀察。
他發現,絕大部分該公司員工在離職後都像消失一樣,他們既不像正常公司一樣擁有離職員工互助群,也不再和公司有任何瓜葛,甚至在交談時也不會主動提到自己的任職公司。
如果不是這次相對規模較大的爭議競業協議糾紛頻繁出現,在權力不對等的勞資關系裡,任何不公的情況都隻能勞動者一人面對,他們既沒有案例參照,也沒有同行者獲得力量。
不過,更現實的一點是,即便有這個 “ 聯盟 ”,他們能做的也並不多。
他們依然是一個抱團取暖的小群體,孤獨地等待接受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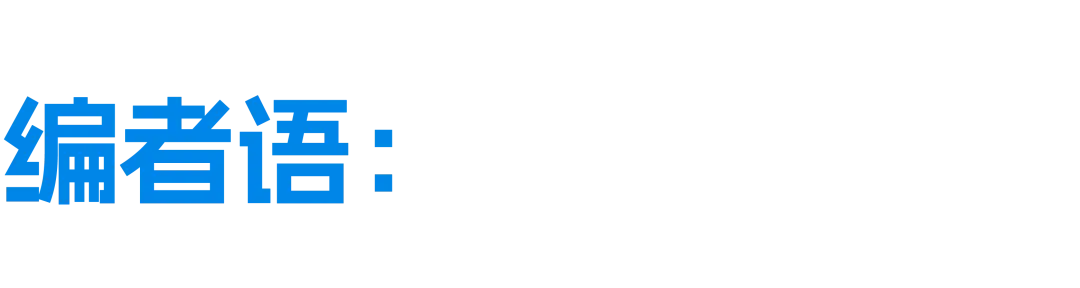
知危編輯部在解這一系列事件時,受到直擊靈魂的震撼。
對於底薪 5900 的小年輕,在被 1770 元/月競業 9 個月的情況下,為生活重新找工作需要賠償公司近 28 萬時,我們發出費解地疑問:他犯天條嗎要如此懲罰?
競業協議是合法的,作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這些人與企業簽訂協議,違反協議後就應當受到懲罰,這無可非議。
但,如果這競業協議本身並沒有那麼合理呢?
勞動者與企業天然就有不對等的關系,不能奢求協議完全對等,但,我們也要考慮一下企業權利的邊際:企業不應持續擴大、濫用自己的權利。
從事實上看,競業協議的擴大和濫用,已然遠超常識認知。知危編輯部接觸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主人公是春節還想著不休息、多打些工多賺些錢的普通打工人李普。
李普在春節期間通過勞務派遣公司進入該公司位於廣東的倉庫,成為一名正式的基層打包工。
簡而言之,就是做產品的打包、整理、入庫等工作。他從沒想到,連他這個打包工入職時也被要求簽訂一份競業協議,如果離職後啟動,競業期限兩年,違反的話將要賠償公司月工資的 24 個月。
這份 “ 機密 ” 工作他打算幹一個月就離開,“ 罰款太多 ”,他說。
這種企業在競業協限制上的擴大和濫用,在勞動者的沉默中持續發展,誰也不知道彈簧何時真正繃裂。
於楓向我們表示,他覺得自己以前是個沉默者,和普通打工族一樣在公司像豬一樣吃飯,然後看到有一天一隻豬被拖走,殺掉,自己也無動於衷,但是很不幸,自己現在成準備被殺掉的那頭豬。“ 但是至少在被宰殺之前,也應該大聲叫出來吧。”
保護企業的權利,非常重要,但保護勞動者的權利,也同樣重要,不應此消彼長。
勞動者不是冰冷的工具,勞動者是一個有自我權利的人。
勞動者不應因入職某一傢公司,經過企業的 “ 培養 ”,就變成企業的某種 “ 私產 ”,進而不能去市場上相對自由的流通。況且,所謂的 “ 企業培養人 ”,本質上也是一種對等的 “ 相互成就 ”,人在工作中同樣創造價值,雙方並無虧欠。
如果著眼於更高的層面來看,企業對競業協議的擴大和濫用,是在抑制整個行業的發展。優秀的人才被不合理的 “ 鎖死 ” 而不能成長或錯失最佳的成長時機,是對人才的一種葬送。
其實,企業並非不能通過其他方式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在科技互聯網同樣發達的加利福尼亞,競業協議是違反州法律的。《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商業和職業法 》第 16600 條規定,除有關公司、合夥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在銷售或解散中的競業禁止協議外,“ 任何人被限制從事任何種類的合法職業、貿易或業務的合同在其范圍內都是無效的 ”。
因此,加州的公司普遍采用 “ 保密協議 ” 以及 “ 知識產權轉讓協議 ” 來保護公司的商業機密和專有技術,這樣既能保護企業的權利,又不阻礙員工的職業發展和行業內的健康競爭。
我們並不認為外國的月亮更圓,也不認為競業協議需要被取消,但我們認為,競業協議的確需要有更明晰的邊際、更合理的權責范圍,以便被被更好地使用。
這應該是同時保護企業和勞動者的協議,而不是一份恐怖的、企業用來 “ 吃人 ” 的協議。